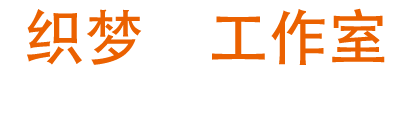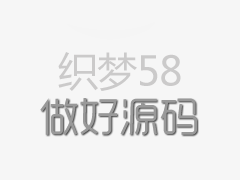《北上》剧:大运河沿岸的一个普通集市及其上
- 编辑:必赢唯一官方网站 -《北上》剧:大运河沿岸的一个普通集市及其上
作者:毛世安(文学评论家) 中央戏剧学院、杭州话剧艺术中心创作的话剧《北上》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小说《北上》。 近年来,由小说改编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小说虽然可以提供优质素材,但改编却极其困难。首先是大小不对称:改编成电视剧,就得在内容上进行“加分”。有观众表示,电视剧版《一路向北》不再和原著一样,成为了“新事物”;适应舞台剧,必须要做“还原”。而且,现在的小说的写法与传统不同。它不再是一个人物的命运和感情,一个家庭的兴衰,或者贯穿整个故事的一条主线。相反,它往往采用许多平行线的结构,并与时间和空间相互作用。 30 号0000字的“北上”是这样的。它与中国人和意大利人、文人、船夫等各种运河人物互动。它将上个世纪城市的平常风俗和国家的兴衰置于现当代不同时期,引人入胜。从小说的案头阅读到话剧的剧场演出,《北上》的改编本身就是一段艰难的“北上”旅程。核心是找到“尊重原作”和“再生阶段”之间的平衡。编剧要在剧本中构建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情境:可以在舞台上表演,故事可以“生机勃勃地站在舞台中央”,反映运河当前的脉搏。运河和海岸景观都流动着。这个“流”既是空间的——剧中,剧在运河以北,经过杭州酒家、扬州古巷青楼、淮安清江浦码头、聊城光月城楼、通州民居等场景;这也是时间性的——从1901年的战争到2014年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繁荣现在。 在改编上,该剧将“原著历史与现在平行”调整为“历史为主、现在为辅”的结构。它大幅删去支线情节,聚焦主线:担任翻译的中国学者谢平遥和搬运工邵昌来陪伴马球少年北上寻找弟弟。这条主线没有金黄的冲突,却隐藏着一个触动人心的戏剧性冲突:在寻找弟弟的路上,波罗不仅受到谢平遥儒家情操的影响,也感受到了邵长来、孙成成等底下人朴实直接的善意。尤其是关于“记忆就是运河”的激烈争论,让波罗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逐渐走进运河的世界和人民。剧中的很多场景堪称“泪珠”:谢平遥与天祥平水的爱情、淮安清江浦粘芦苇旁天祥墓前的追悼会、小波罗在通州客轮上的遗言。次要情节围绕后代展开。孙彦霖与谢的争论让位于“如何保存运河的记忆”,船夫邵秉义卖船事件与主线呼应,勾勒出当代运河的生命力与思想。编剧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文学描述转化为设定的戏剧情境,让人物通过直接的言语和行动、对抗和交流,将文字的清晰转化为有形的视听张力。 文学改编戏剧主要有两个步骤:小说到剧本,从剧本到戏剧。小说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剧本的成功,但剧本的成功也意味着剧场的成功是不可替代的,而《北上》取得了这种“双成功”。杭州话剧艺术中心虽然不是著名的剧团,但数十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演员却将全部热情投入到舞台和角色中。每个人都力求“使自我与性格的灵魂融为一体”:波罗从陌生多疑到信任托付的心理转变,谢平遥的冷静豪爽的儒家风范,小船的诚实质朴,以及天香等女性人物的纯洁灵魂。即使是小角色也被描绘得精确而可信。经过数十次巡演,演员们对人物和台词的处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就连台上一声叹息的微妙反应也很准确。 舞台设计“北上”的标志形象更美,主要标志是“船”。这种简单的装置采用榫卯结构,可以拆卸、旋转、升降。它具有现代艺术的感觉,并且有多种解释的空间。船不仅是大运河的载体和体现,也是故事的主要背景。堪称“不会说话的主角”:主要故事发生在船舷上。正如导演的诗句:“升起,像一段悬浮在时间里的记忆;转身,让晚清船只与当代游轮相遇;沉没,将百年悲欢隐藏在水中。”当在通州船舱里闭上小波罗的眼睛时,一百年后,孙燕来到同一个码头,拾起船上的旧木板,舞台的空间和时间“折叠”了。此外,“摄像头”的反复出现也有深意:从最初的“恐惧”大家好,几代人在聊城光月楼前的合影,按下快门的那一刻,就是文化隔阂消解的隐喻。 该剧运用的舞台技巧极其丰富。歌剧、快板、船家号子、多媒体等,大家都出现在舞台上,但纷繁而不乱。它们同频反映了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情绪:灯光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心情,古筝的声音如流水,小提琴的音乐温柔而悲伤;诗句之间的沉默留下了足够的思考空间。历史与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集(如前几代聊城光月楼同框)处理得自然恰当,舞台设计采用了现代绘画的“硬边”。清江浦纪念馆场景中出现冷色色块和沙沙作响的芦苇天空中,直击人心。这些创新形式相互兼容,形成有机统一的审美场域,就像自然生长的“蔬菜”。 小波罗没有见到弟弟,留下了遗憾,但有一次他小声对弟弟说:“我去过你去过的每一个城市,见过每一个中国人,走遍了整条运河。”话剧《北上》与这部《运河》有相似之处。在剧场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可以听到大运河数百年来绵绵不绝的水声,体会其中的文明与温暖。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9日第14页)